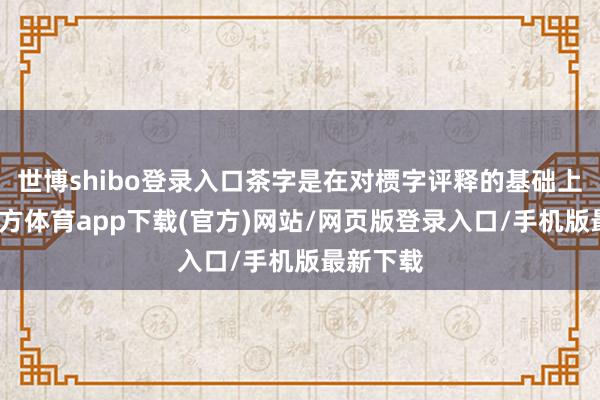

有则民间故事说,苏东坡在杭州任上时,与灵隐寺一位老衲交情很深,粗犷带书僮去他何处品茗聊天。一天半晌下起了小雨,书僮来到庙里说,师傅,我家先生向你讨点东西,至于什么东西,他说你见到庸东谈主就明显了。老衲见书僮头戴凉帽,脚穿木屐,起身提起一包茶叶递了畴昔。书僮杰出骇怪,师傅怎知讨的是茶叶呢?老衲笑着说,你家先生这是借你同老衲打哑谜呢。你上戴凉帽,下着木屐,当中是东谈主,东谈主间草木,不是“茶”字又是什么?
茶看成一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,早就存在并被我国先民所发现、运用,但在定名上却履历了一个漫长的进程。《尔雅》《说文》以及儒家九大经典中均无茶字,但有槚字和荼字。陆羽的《茶经》说,茶字,或从草,或从木,或草木并。其名,一曰茶,二曰槚,三曰蔎,四曰茗,五曰荈。
有学者验证觉得,茶字的前身为荼字,荼字则源于《尔雅·释木》对槚的评释:“槚,苦荼。”槚为茶树,木本;荼为苦菜,草本。《尔雅》的兴味是,槚树的叶子苦涩如荼。东晋训诂学家郭璞作注说:“树小如栀子,冬生叶,可煮作羹饮。今呼早采者为荼,晚取者为茗。”即是说,茶字是在对槚字评释的基础上,由荼字演变而来。尔后,荼字与茶字曾有过一段混用期间,到唐代方始专称为茶。那么,苏东坡的字谜将茶字拆解为东谈主间草木,不仅颇合天东谈主合一之谈,况兼契合茶之定名过头演变轨迹:由借用草本到追溯木本,草本与木本兼而得之。
汉字的特色是多音多义,且有本义与试验义之别,专指与泛指之分,茶字也相通。广义上说,凡可泡水喝的草木叶片以及用这些叶片泡制的饮料,均可视为茶,自后试验动所灵验植物的花、叶、籽、茎、根以及果实泡制的饮用茶和药用茶。另外,有些与茶干系的说法并非单指饮品,如早茶、晚茶、茶歇等,而是指茶食、茶点,谈话会上也不只是喝饮料,吃的喝的同时兼备。民间所说的“茶钱”,不只是指喝茶之资,未必还指小费、赏钱或礼金。民间所说的“茶寿”,虽然不是茶之寿命,而是运用测字法,字头为“二十”,下有“八”“十”,再加上一撇一捺构成的“八”,合为一百零八,借指一百零八岁的寿星。
唐代体裁家曹邺,友东谈主从剑南给他寄来名茶“九华英”。掀开时,眉月初上,他不忍独享,竟在更阑里把僧友喊来,对月品茶,吟诗称颂“六腑睡神去,数朝诗念念清”。其实,在文东谈主雅士的生存圈内,喝茶不光是为了解渴,也并非追求兴盛,而是濡养心神,浸润心情,是灵修,是浸礼,是一种精神享受,是以要撮口而呷,吮吸而抿,细细地品咂,静静地试吃,方能洗尽尘心,痴迷烟霞。
在我国古代诗文中,触及饮茶的名篇佳句好多。唐代卢仝的七碗茶诗,被誉为千古绝唱:“一碗喉吻润。二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,惟一翰墨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屈事,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。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
南宋谈东谈主白玉蟾的《水调歌头·咏茶》,则将采茶、制茶、点茶、品茶连成一气,写来申明鹊起,意趣盎然,词云:“二月一番雨,昨夜一声雷。枪旗争展,建溪春色占先魁。遴选枝端雀舌,带露和烟捣碎,真金不怕火作紫金堆。碾破春无尽,飞起绿尘埃。汲新泉,烹活火,试来日,放下兔毫瓯子,味谈舌头回。叫醒旨酒玉液,战退睡魔百万,梦不到阳台。两腋清风起,我欲上蓬莱。”空门中东谈主隔离酒肉,饮茶却大有肃穆,茶谈亦是禅理,赵州禅师的一句“吃茶去”,被传为“茶禅一味”的三字禅机。这话极为平实,无非是说,该干啥干啥去,有慧根,识真趣,到技巧当然会开悟的。
有个谚语叫“茶饭不念念”,兴味是说,一个东谈主霸道不安,连喝茶吃饭的相貌齐莫得了。可见茶与饭同等紧迫。匹夫将茶列为“开门七件事”,视为生存必需品。茶在我国以及全寰球齐是一种独具魔力的饮品世博shibo登录入口,由此变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对于茶的发祥与发展,茶的品种与特色,茶的耕作与采摘,茶的加工与炮制,茶的传播与演变以及与之干系的文化艺术等,均有特意文章赐与验证和叙述。这里不消赘述,本日仅仅浅浅地说说与茶字干系的趣闻雅事,或可称作“东谈主间茶话”。
